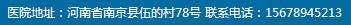当前位置:肺炎球菌感染 > 检查诊断 > 日本quot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治疗指 >
日本quot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治疗指
本文原载于《中华内科杂志》年第4期
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是一种患病率高、病死率高的重要疾病。根据美国的调查每年每个人中有12人患上肺炎,在日本每天肺炎的接诊率为每10万人口25人[1]。美国、欧洲、我国都先后出版了CAP的诊治指南[2,3,4]。国内外对CAP的认知和临床诊治总体上是一致或相似的。日本呼吸器官学会呼吸器官感染症指导方针编写委员会年出版了日本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治疗指导方针,并在年再版并进行了完善更新[1]。该方针与我国广泛使用的CAP指南有诸多相同的原则和规范,亦有不同之处,现就其中主要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供读者思考和实践。
一、CAP的诊断
肺炎是一种肺实质受到急性感染的感染性炎症。典型病例会出现咳嗽、咳痰、胸痛、呼吸困难等局部症状和发烧、乏力等全身症状,但是在年龄或基础疾病等因素的影响下,并非都能够观察到典型的症状。在老年人中,呼吸频率增加、心动过速、食欲减退、精神低迷、沉默寡言等症状都可能是肺炎所致。可反映出急性炎症的血液检查[WBC、C反应蛋白(CRP)、ESR等]能客观地表现出炎症的存在,可以对肺炎进行定性诊断,并且帮助与其他疾病的鉴别诊断。CAP医院获得性肺炎、肺结核、吸入性肺炎、阻塞性肺炎、在老年人机构等疗养院发病的肺炎、慢性下呼吸道感染的急性恶化等。
(一)胸部影像学检查在CAP诊断中的地位
欧洲学者认为出现下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患者非常常见,但肺炎仅占10%以下,出于卫生经济学的考虑,推荐在患者出现新的局限性胸部体征、呼吸困难、呼吸频速、发热4d、脉搏次/min等情况时再考虑胸部X线检查。并且认为患者如CRP20mg/L、且症状持续时间24h,那么患肺炎的可能性极低;如CRP浓度mg/L,即有可能是肺炎,如完成CRP检查后仍无法确诊,则考虑进行胸部X-线检查[4]。在美国和我国的CAP指南中则将胸片显示的肺部炎性浸润病灶作为确诊CAP最重要的依据[2,3]。日本的指导方针指出因为CAP临床表现的非典型性,在发现疑似症状时,应该尽早让患者接受胸部影像检查。并且强调胸部CT检查在胸部X线难以发现阴影或需要更加详细了解胸部异常阴影性质时是非常有价值的[1]。
(二)病原学检测在CAP诊断中的地位
CAP病原学检出阳性率低,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和增加临床费用。欧洲下呼吸道感染治疗指南不建议在CAP患者中常规进行诸如培养和革兰染色等微生物学检查、不建议在初级医疗保健机构内进行细菌性病原体生物标记物评价,包括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血清学及PCR检测、肺炎链球菌抗原检测[4]。美国感染病学会与美国胸科学会也一致主张在门诊和社区诊所诊治的CAP不必进行病原微生物检测,但同时指出微生物学检测结果可能有助于改变抗生素处方,在可预见检出率较高患者中可进行相应检测[3]。对于住院患者多数学者主张进行痰培养、涂片镜检和血培养,尤其对于中、重症CAP需要进行血培养、军团菌抗原检测等。日本CAP指导方针则认为致病微生物的鉴定和药物敏感性检查是十分重要的,建议进行积极的微生物学检查,但应在微生物学标本采集后即进行经验性治疗,并参考涂片检查、抗原检查、培养及药敏结果进行调整。具体检测的指导意见如下[1]:
1.微生物学检查标本的获得:
供微生物检查之用的标本最好是接受抗菌药物治疗前所采集的,包括咳痰等来源自呼吸道的标本、血液和尿液标本。应当采集来源于病灶部位的脓性痰,由于咳出过程中容易受到上呼吸道的常驻菌群引起的感染,因此必须评估咳出的是否适合微生物检查。当遇到咳痰较难的情况时,可以尝试在患者雾化吸入后让其咳出痰标本,也可采用经气管穿刺抽吸法、气管内采痰法、支气管肺泡清洗法、经支气管肺活检、经皮细针穿刺抽吸法等方法采集标本。此外,当遇到疑似结核的情况时,除了可直接从痰或病灶中获得的标本外,胃液、咽拭子也有价值。
2.有助于初期治疗的微生物检查(快速检查):
快速检查可大致分为简单方便且可在门诊、病床边予以实施的检查(分为精度不太容易受到检查实施者经验影响的检查以及精度很容易受到检查实施者经验影响的检查)和操作方法较为复杂或者需要特定的医疗仪器、设施的检查。
(1)简单方便且可以在门诊、病床边予以实施的检查:精度不太容易受到检查实施者经验影响的检查:目前,市面上已有出售在快速诊断方面有助于检测出抗原且可以从标本中直接鉴定出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A组溶血性链球菌、肺炎球菌、军团菌(免疫层析法)的试剂盒。由于这些抗原检查的操作方法十分简单方便,并且判定时间也只需数分钟到最长约3h不等,因此在门诊或者病床边也可以充分实施。
精度很容易受到检查实施者经验影响的检查:包括痰涂片细菌革兰染色以及一些也可以通过其他的特殊染色法来进行鉴定的病原体,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结核分枝杆菌、军团菌、真菌、耶氏肺孢子菌等。尤其是军团菌的希门尼斯染色、耶氏肺孢子菌的Diff-Quik?染色、姬姆萨染色操作起来非常简单方便,在门诊或者病床边也可以实施一些特殊染色。
(2)操作方法较为复杂或者需要特定的医疗仪器、设施的检查:涂片镜查:除了革兰染色外,真菌在PAS染色、六胺银染色下也可被染色。除了Diff-Quik?染色法之外,耶氏肺孢子菌在姬姆萨染色法、甲苯胺蓝染色法、六胺银染色法下也有可能会被染色。荧光(金胺罗丹明)染色法的灵敏度比Ziehl-Neelsen抗酸杆菌染色法高10~倍,非常适合用于结核筛选检查。使用荧光抗体法可以使用从痰等呼吸道分离标本中检测出军团菌、衣原体、耶氏肺孢子菌,或者使用咽拭子在荧光显微镜下检测出肺炎支原体。
抗原检查:可以使用ELISA法检测腺病毒、采用酶抗体(EIA)法检测出被排泄到尿液中的军团菌特异抗原。曲霉菌、隐球菌、念珠菌等真菌和巨细胞病毒也可以从血清中(隐球菌也可以从脊髓液中)检测出抗原。
基因检查:由于结核分枝杆菌、非结核性抗酸菌、肺炎支原体、军团菌在培养检查中需要较长时间,而衣原体、耶氏肺孢子菌培养是比较困难的,可以采用基于DNA探针法或者PCR法等方法检测。也可以采用PCR法从血液中检测巨细胞病毒。
3.结果明确前需数日的微生物检查:
培养鉴定和药物敏感性试验:包括普通细菌培养以及普通细菌以外的特殊病原体如:结核分枝杆菌、军团菌、支原体等。以结核分枝杆菌为首的抗酸菌或军团菌、肺炎支原体不会在通常的培养基中发育,需要分别使用特殊的培养基。药敏结果则通常需要经过数天或者十几天。
抗体检查:在对由抗体效价上升引起的感染进行诊断的过程中,必须测定急性期和1~2周后的恢复期的双份血清并对4倍以上的上升情况进行确认。在测定血液中的特异抗体效价时,用于诊断分析的病原体包括有各种病毒、衣原体、肺炎支原体、军团菌以及考克斯体属。
(三)CAP疾病严重程度的诊断
肺炎严重程度的判断是诊断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几乎所有CAP管理相关的决定,包括诊断与治疗,都由对病情的最初评估决定。疾病严重程度评分[如CURB-65标准(意识模糊、呼吸频率、低血压、≥65岁)],或预后模型(如PSI)以及美国感染性疾病协会(IDSA)重症肺炎的主要和次要标准可用于确定哪些CAP患者在门诊、住院或者入住ICU治疗并可预估患者的死亡风险[3]。在欧洲及美国的指南中均推荐使用上述评分标准,并强调客观标准与医生根据主观因素(患者安全、可靠地进行口服治疗的能力,及有无可利用的门诊支持资源等)所做的决定相结合。虽然评分有助于住院决策,但仅靠评分就做出决定是不安全的。动态地长时间观察比某一个时间点的评分有助于更准确地做出决择。日本CAP指南中提出CRP、WBC、体温等参数无法正确反映出严重程度,IDSA的指导方针可以正确反映出预后情况,但是分数计算太过复杂。因此,日本指南依据CURB-65系统并进行了适当的修订,形成了适合其国家的标准。具体指标包括:男性70岁以上,女性75岁以上;尿素氮21mg/dl以上或者有脱水症状;脉搏血氧饱和度(SpO2)90%以下[PaOmmHg(1mmHg=0.kPa)以下];意识障碍;血压(收缩压)90mmHg以下;轻度CAP:不符合上述5个项目中的任意一项;中度CAP:符合上述5个项目中的1项或者2项;重症CAP:符合上述5个项目中的3项;超重症CAP:符合上述5个项目中的4项或者5项;但是,如果有休克症状,即可视为超重症。符合≥2项需要考虑住院治疗,符合≥4项需要考虑入住ICU[1]。
(四)细菌性肺炎和非典型性肺炎的鉴别
日本呼吸器官学会指导方针中规定了针对细菌性肺炎与非典型性肺炎(主要指支原体和衣原体肺炎,不包括军团菌肺炎)的鉴别方法,这是其独有的见解[1]。欧美的指南中鉴于CAP的致病微生物尤其是非典型性病原体的频率在各年龄层不会发生变化、细菌性肺炎和非典型性肺炎难以通过临床表现或胸部X光照片进行鉴别、两者之间经常发生混合感染等原因,并没有对两者进行鉴别[3,4]。日本指南对两类肺炎进行鉴别的原因为:大多数的肺炎球菌性肺炎可以通过在临床上输注β-内酰胺类药物(青霉素类药物)来予以治疗;日本国内的支原体肺炎多发生于年轻人群,肺炎球菌的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耐药水平要高于欧美国家,实际上专业医师在临床现场都会先进行鉴别然后再实施治疗。因此认为对两者加以鉴别区分是很有必要的。细菌性肺炎和非典型性肺炎的鉴别标准[1]:(1)年龄低于60岁;(2)无基础类疾病或者症状轻微;(3)有顽固性咳嗽;(4)胸部听诊未闻及明显啰音;(5)无咳痰或者在快速诊断下未发现疑似致病菌的细菌;(6)末梢血WBC低于0/μl;(1)~(5)项中≥3项为阳性者疑似非典型性肺炎,≤2项为阳性者疑似细菌性肺炎;(1)~(6)项中≥4项为阳性者疑似非典型性肺炎,≤3项为阳性者疑似细菌性肺炎。
将6个项目中的4个以上的项目相符的情况诊断为疑似非典型性肺炎是最为合理和妥当的,支原体肺炎的灵敏度为86.3%,肺炎衣原体肺炎的灵敏度为63.1%,总计非典型肺炎整体的灵敏度为77.9%、特异度为93.0%。另一方面,考虑到WBC并不一定能够在短时间内查明并加以利用,因此将除该项目以外的其他5个项目中的3个以上项目相符的情况规定为疑似非典型性肺炎,灵敏度为83.9%、特异度为87.0%。即使采用了该诊断标准,也经常会遇到难以鉴别开细菌性肺炎和非典型性肺炎的情况。指导方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筛检出典型的非典型性肺炎,然后采用大环内酯类或者四环素系抗菌药物实施治疗。还有很高的几率出现非典型性肺炎与细菌性肺炎的混合感染,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在临床方面多会呈现出细菌性肺炎的临床表现。如果在根据该指导方针进行鉴别并输注抗菌药物后病情仍无法得到改善的话,那么也应当探讨是否需要输注其他类的药物,或者有必要根据病例的实际情况考虑采用联合治疗。
(五)关于军团菌肺炎
军团菌是一种由属于葡萄糖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但无法在革兰染色法下被检测出来,而且β-内酰胺类药物对其不起到任何作用,因此在临床方面被归入到了非典型性肺炎中。但在日本的指导方针将军团菌肺炎视作为了细菌性肺炎[1]。在日本,军团菌肺炎占成人CAP中的3%,其中约90%是由嗜肺军团菌血清1型引起的。军团菌肺炎的病情发展非常迅速,有可能趋于严重化、预后较差,致死率甚至达到了约15%,因此是属于必须引起注意的肺炎。军团菌肺炎病初常表现为倦怠感、头痛、肌肉疼痛、干咳,经过2~10d的潜伏期后,多会出现伴有寒战、高热,并逐渐有痰产生,大多数情况下呼吸困难的症状会进一步恶化。容易伴有腹泻、相对脉缓或中枢神经系统障碍。胸部X光检查结果多种多样,在重症病例中,会表现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阴影,同时伴有强烈的呼吸困难。最推荐使用的是可简单方便且快速检测出尿抗原的试剂盒,检测率可达到约70%。对于重症病例,建议使用新型喹诺酮类注射药物、大环内酯类注射药物,对于症状较轻的病例,可以使用新型喹诺酮类口服药物或大环内酯类口服药物。使用周期约为2~3周。
二、CAP的治疗
日本指导意见中强调了以抑制耐药性细菌为目的,贯彻了不将具有广谱及强杀菌力的新型喹诺酮类药物和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作为经验性治疗的首选药物的基本思路[1]。具体将治疗分为经验性治疗及目标治疗两个层级。并根据患者的高危因素进行分层[1]。
(一)经验性治疗时的抗菌药物选择
1.成人CAP初期治疗的基本流程见图1。
2.对于在门诊治疗的疑似细菌感染CAP。如没有基础类疾病及耐药菌感染高危因素的患者使用含β-内酰胺酶抑制剂的青霉素类口服药物,如果在3d的后续观察期内病情未有改善且症状没有出现恶化,可以考虑并用大环内酯类药物,或者改为使用呼吸喹诺酮类药物。如果症状出现恶化,建议改用呼吸喹诺酮类药物,或者住院接受治疗。年龄在65岁以上或者控制良好的基础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肾脏疾病、肝脏疾病),选用含β-内酰胺酶抑制剂的青霉素类口服药物±大环内酯类或者四环素类口服药物,由于在高龄者人群中,有时会发生无法否定肺炎衣原体的感染的情况,因此需要在认定确有必要的情况下予以联合。慢性呼吸道疾病、最近接受过抗菌药物给药或者有青霉素过敏史患者给予呼吸喹诺酮类口服药物。在门诊时需要使用注射类药物可以考虑头孢曲松。
3.对于住院治疗的疑似细菌感染CAP。未患有基础类疾病或者患者为年轻成人考虑给予含β-内酰胺酶抑制剂的青霉素类注射药物。年龄在65岁以上或者患有轻微症状的基础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肾脏疾病、肝脏疾病)的将头孢类药物也加入到选择项中。对于患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在将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注射用喹诺酮类药物也加入到选择中。如果在实施治疗3d内发烧等症状仍未得到改善的话,应当在参考治疗开始前的细菌学检查结果的基础上考虑更改抗菌药物。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增加可有效治疗非典型病原体的抗菌药物(大环内酯类药物、四环素类药物等)。
4.对于在门诊治疗的疑似非典型性肺炎。未患有或者患有轻微症状的基础类疾病、或者患者为年轻成人给予大环内酯类药物、四环素类口服抗菌药物,如果在3d的后续观察期内病情未有改善,则改用含β-内酰胺酶抑制剂的青霉素类口服抗菌药物。如果无法使用大环内酯类药物或者四环素类药物的话,则可以使用呼吸喹诺酮类药物。年龄在65岁以上或者患有慢性呼吸道疾病、心脏疾病的患者除大环内酯类药物、四环素类口服抗菌药物外可以考虑选择呼吸喹诺酮类口服药物。
5.对于住院治疗的疑似非典型性肺炎。住院治疗的情况下大环内酯类药物、四环素类药物、新型喹诺酮类注射药物如果在3d治疗期内病情未见好转或者患有慢性呼吸道疾病、心脏疾病的患者可以选择大环内酯类口服药物或者呼吸喹诺酮类药物±第2、3代头孢类注射药物。
6.重症肺炎。应尽快输注可治疗肺炎链球菌、克雷伯菌、绿脓菌、军团菌、支原体、鹦鹉热的抗菌药物。根据患者的病情从1组(碳青霉烯类注射用抗菌药物、第4代头孢类注射用抗菌药物+克林霉素、第3代头孢类注射用抗菌药物+克林霉素、单酰胺类注射用抗菌药物+克林霉素、糖肽类注射用抗菌药物+氨基糖苷类注射用抗菌药物)和2组(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四环素类抗菌药物、喹诺酮类抗菌药物)的抗菌药物中选择合适的抗菌药物进行联合。
(二)致病菌判明时的抗菌药物选择
1.肺炎链球菌:
肺炎链球菌的治疗在日本以青霉素类抗菌药物为原则,对于敏感性下降的给予高剂量给药。当需要将以流感嗜血杆菌为首的革兰阴性细菌也包括在内并实施治疗时,通常使用的是含β-内酰胺酶抑制剂的青霉素类。碳青霉烯类、万古霉素等也具有优良的抗菌力。弄清药物敏感性后,选择以下所示的注射液药物:若为高水平青霉素耐药肺炎链球菌(PRSP,青霉素G4μg/ml):碳青霉烯类药物、万古霉素、利奈唑胺;青霉素低敏感性或者敏感性(青霉素G2μg/ml):增量使用青霉素。
2.流感嗜血杆菌:
在无药敏感结果时选择口服给药可考虑第3代头孢类药物或者新型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在注射药物方面,应当根据严重程度选择哌拉西林,含β-内酰胺酶抑制剂配方的青霉素类药物,第2、3代头孢类药物,碳青霉烯类药物,新型喹诺酮类药物。如有药敏结果时,应当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窄谱抗菌药物。
3.卡他莫拉菌:
选择口服给药时,选择顺序依次为大环内酯类药物、含β-内酰胺酶抑制剂配方的青霉素类药物、第2、3代头孢类药物。在选择注射药物时,选择顺序依次为含β-内酰胺酶抑制剂配方的青霉素类药物、第2、3代头孢类药物。虽然碳青霉烯类药物和喹诺酮类药物也是很有用的,但是应当只有在重症病例和基础类疾病并存的情况下选择使用。
4.金黄色葡萄球菌:
对于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MSSA),应当选择使用β-内酰胺酶抑制剂配方的青霉素类药物、第1、2代头孢类药物。确认是由于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引起的肺炎,则适合使用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利奈唑胺。
5.铜绿假单胞菌:
拥有铜绿假单胞菌抗菌活性药物包括青霉素类药物或者头孢类药物、或单酰胺类药物、碳青霉烯类药物。也可以选择氟喹诺酮类药物。
6.克雷伯菌:
日本可以产生超广谱β-内酰胺酶的菌株较少,含β-内酰胺酶抑制剂的青霉素类、第2代头孢类、第3代头孢类药物、碳青霉烯类药物或新型喹诺酮类药物均可以作为选择。
7.厌氧菌:
在吸入性肺炎中,如果出现了咳痰有恶臭、有空洞形成等病状,则怀疑可能与厌氧菌有关。可使用含β-内酰胺酶抑制剂配方的青霉素类抗菌药物、克林霉素或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
三、疗效判断和疗程
CAP治疗效果的判定时间点和主要判定事项在日本指南中有如下建议[1]:治疗开始3d后(重症病例为2d后)的判定:初期抗菌药物的有效性评价、7d内的判定:有效性评价以及决定结束时间、14d内的判定:结束时间以及药物更改的决定。效果判断的指标和标准包括4个:退烧(目标:37℃以下)、末梢血WBC增加的改善(目标:正常化)、CRP的改善(目标:下降到最高值的30%以下)、胸部X线阴影有明显吸收。抗菌药物给药结束时间需要结合治疗效果的判断:不存在明显的基础类疾病者符合4个效果判定基准项目中的3个以上的项目,存在明显的基础类疾病者符合4个效果判定基准项目中的3个以上的项目的4d后。指南指出上述目标和标准得到了部分委员的反对意见,其一认为该标准不能缩短抗菌药物的使用疗程,其二认为CRP的价值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于从静脉到口服给药的转换时期,改指南引用了年美国感染病学会发布的指导方针中的规定。当患者处于以下状态时,可以改为口服药物给药:临床症状明显改善、可以摄取药物、血流动态趋于稳定、胃肠道功能明显改善。
对于出院时间的问题,指南认为可以将抗菌药物的停药时间视为出院时间。对于未患有基础类疾病的患者,可以考虑将注射药物改为口服药物时安排患者尽早出院。结合美国感染病学会发布的指导方针中的规定,如果尚未退烧(37.8℃以上),心率在次/min以上,呼吸频率在24次/min以上,收缩压在90mmHg以下,血氧饱和度在90%以下,无法口服给药中的2个以上的条件,则不能让患者出院。出院的患者仍需要后续观察。患有重症肺炎或者支原体肺炎、衣原体肺炎、军团菌肺炎、慢性呼吸器官疾病的肺炎等患者,可能会在治疗后出现再次恶化的情况。欧洲的医疗机构通常会在从抗菌药物给药结束到2~4周后的期间内对患者进行缜密的后续观察,以此来弄清是否存在复发现象,之后再予以最终评估。日本的指南则希望实施至少1周的后续观察,之后再给出最终的评价。
参考文献(略)
(收稿日期:-12-24)
(本文编辑:胡朝晖)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