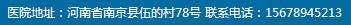当前位置:肺炎球菌感染 > 症状体现 > 读城宋代成都之六岁时记,夏市与时尚日 >
读城宋代成都之六岁时记,夏市与时尚日
林元亨/文
白郎林元亨邓平模/供图
秋分天渐凉。告别暑热,走进秋天,成都的天气一下子就凉爽怡人。这时候,摊开一幅宋画,可遥观宋代成都人挥之不去的夏之热烈。或许,成都人的夏天,需要在夏秋之交,在成都平原的打谷声中,来一一讲述与回溯:浴佛日、浣花遨头、天中节、江渎庙祭祀,锦市、扇市、药市、香市。南宋宁宗庆元三年()的夏天,宣和画院宫廷画家李迪,画了两幅《红白芙蓉图》,画境中粉红嫩白的两色芙蓉花,亭亭欲滴飘摇于晴空,花儿光彩灼灼,让人遥想旧时锦官城头,后蜀君王孟昶为花蕊夫人种植的那些芙蓉花。比李迪稍晚的另一个宫廷画家李嵩,画过《花篮图》,里面有一幅夏花,精致的竹篮里,放着蜀葵、栀子、百合、石榴花,令人追念蜀中的夏日光景。李迪、李嵩的作品,明显受到五代宋初时期西蜀画家黄荃父子的影响,他们笔墨下真切而遥远的的鲜花,把我们的视线,引向宋代成都活泼而蓬勃的夏天。
▌成都当代肖氏蜀绣《女十忙》邓平模摄
浣花遨头,四月锦市濯锦江头,碧浪淘沙,千门万户,绮陌尘香。
《宋高僧传》说:“蜀土尤尚二月八日及四月八日。每到二时,四方大集,驰骋游遨。”二月八日是释迦牟尼佛出家的纪念日,四月八日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日。这两个日子,也变成了蜀人云集游玩的日子。
有一幅相传是北宋画家苏汉臣画的《灌佛戏婴图》,就画着孩童们有的手持盛着月季花朵的小花盆作为供养,有的把瓶中的水倒出来沐浴佛像。还有一瓶灵芝,已经供养在佛像前。
写过《桃花扇》的孔子六十四代孙、清人孔尚任的《节序同风录》则记载说,“浴佛日”这天一早,“采芍药花供佛,谓之浣花天。”
“浴佛”这一天,宋代的成都人是怎么过的呢,史料没有更多的记载。或许正像《东京梦华录》所写:“迤逦时光昼永,气序清和。榴花院落,时闻求友之莺。细柳亭轩,乍见引雏之燕。在京七十二戸诸正店,初卖煮酒,市井一新。唯州南清风楼,最宜夏饮……”
四月十九日,对成都人来说,是浣花佑圣夫人的生日。“太守出笮桥门,至梵安寺谒夫人祠,就宴于寺之设厅。既宴,登舟观诸军骑射,倡乐导前,泝流至百花潭,观水嬉竞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帟(帐子)水滨,以事游赏,最为出郊之胜。”宋祁有《忆浣花泛舟》诗,田况有诗《四月十九日泛浣花溪》。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最盛于他时。”从开年开始的宴游,终于到了这一天结束了。而在老百姓眼中,最为灵验的是,每年的这一天都是一个大晴天,“蜀人云:虽戴白之老,未尝见浣花日雨也”。
▌南宋李迪《红白芙蓉图》之“红芙蓉”,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南宋李嵩《花篮图》之“夏花”,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浣花夫人,成都任氏女子,喜弓马,善骑射,其夫崔盱于唐大历二年()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次年,崔旰入朝奏事离川,泸州刺史杨子琳趁机攻打成都,任氏英勇出战,击溃杨子琳,成都得以保全。朝廷加封崔旰为冀国公,封任氏为冀国夫人。相传她本是浣花女,老百姓就称之为“浣花夫人”。后来就为其在梵安寺内建“佑圣夫人祠”。梵安寺,隋名桃花寺,后名浣花寺,北宋改为梵安寺,明时俗称草堂寺。《方舆胜览》载:梵安寺“在成都县南,与杜甫草堂相接。每岁四月中浣前一日,太守宴集于此”。宋人谢采伯《密斋笔记》说:“夫人能散财破贼人杨子琳,邦人德之,即所居祠夫人。后草堂与祠并称。”
自前后蜀时期,四月十九拜佑圣夫人游浣花,就成为一种风尚,如张唐英《蜀梼杌》记载,前蜀“游浣花溪,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后蜀“蜀中百姓富庶,夹江皆创亭榭游赏之处。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绮罗,名花异香,馥郁森列”。宋人任正一的《游浣花记》说:“成都之俗,以游乐相尚,而浣花为特盛。每岁孟夏十有九日,都人士女,丽服靓妆,南出锦官门,稍折而东,行十里入梵安寺,罗拜冀国夫人祠下,退游杜子美故宅,遂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因名其游与其日。凡为是游者,架舟如屋,饰彩绘,连樯衔尾,荡漾波间,箫鼓弦歌,喧闹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结棚,上下数里,以阅舟之往来。成都之人,于他游观或不能皆出,至浣花则倾城皆往,里巷阗然。自旁郡观者,虽负贩刍荛之人,至相与称贷,易资为一饱之具,以从事穷日之游。府尹亦为之至潭上置酒高会,设水戏竞渡,尽众人之乐而后返。”庄绰《鸡肋篇》记载:“浣花自城去僧寺凡十八里,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两岸皆民家绞络水阁,饰以锦绣。每彩舟到,有歌舞者,则钩帘以观,赏以金帛。以大舰载公库酒,应游人之计口给酒,人支一升,至暮遵陆而归。”当天,“往昔太守分遣使臣以酒均给游人,随所会之数以为斗升之节。”这样的举措,促进了活动的氛围,也带动了老百姓的消费。
▌宋代《女孝经图》(局部)
▌日本镰仓建长寺收藏的古代蜀锦
▌锦里织锦青青容颜摄四月,成都人岁岁要办锦市。西晋左思《蜀都赋》说:“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起点的成都,以锦擅名天下,所以名“锦官城”,江也因“濯锦”而成锦江。
《宋会要·食货》称:“蜀土富饶,丝帛所产,民织作冰纹、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宋代太平老人撰《袖中锦》说,蜀锦为天下第一。宋时,成都不但有“成都府锦院”(转运司锦院)与“茶马司锦院”,还有“锦机玉功不知数(陆游《晚登子城》)”。元费著《蜀锦谱》里,就记载蜀锦种类近四十种,如上贡用锦,有盘球锦、簇四金雕锦、葵花锦、八答晕锦、六答晕锦、翠池狮子锦、天下乐锦、云雁锦,民间流行的,则有穿花凤锦、百花孔雀锦、如意牡丹锦、落花流水锦等。
另外,上贡用锦还有一种灯笼锦。纹样以灯笼为主体,饰以蜜蜂、流苏图案。流苏乃谷穗的变形,代表五谷,而蜜蜂的“蜂”、灯笼的“灯”则分别谐音“丰”“登”,联成“五谷丰登”的吉祥寓意。皇祐三年(),御史唐介揭露文彦博,说他送了蜀锦给宋仁宗的张贵妃,所以才有升迁的机会。文彦博送的就是灯笼锦。据梅尧臣《碧云騢》说,上元节这天,张贵妃还特意穿着灯笼锦做的衣裳,去见仁宗,并说此锦是益州知州文彦博特意织就来献给皇帝的。
两宋时,蜀地锦市是如此盛名,所以,吕大防在《锦官楼记》写道:“蜀居中国之西南……土地之毛,善利丝枲(麻),为之缯布,以给上国。……日输月积,以衣被于天下。”并描述“锦官城”当时的作坊盛况:“连甍比室,运箴弄杼,燃膏继昼,幼艾竭作,以供四方之服玩。”这正是“扬一益二”的成都:“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
天中节与五月扇市五月,端午前后,成都人家种在房前屋后的蜀葵在平原上开花了。端午,民间又俗称“端阳”,宋人多称“天中节”。“端午”的“端”字本义为“正”,“五”(午)为中。“端午”(端五)即“中正”,这一天午时则为正中之正。据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熙朝乐事》载,端午为天中节,是因为午日太阳行至中天,达到最高点,午时尤然。这一天,人们还会把艾草挂在门扉上,女孩儿们会玩斗草的游戏。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宋代的成都人和其他地方的宋人一样,要过一个热热闹闹的端午节:“五月五日,宴大慈寺设厅。医人鬻艾,道人卖符,朱丝彩缕、长命辟灾之物,筒饭角黍,莫不咸至。”孟元老作于宋钦宗靖康二年()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的端午节物,有百索艾花、银样鼓儿花、花巧画扇、香糖果子、粽子、白团。紫苏、菖蒲、木瓜,并皆茸切,以香药相和,用梅红匣子盛裹。“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与五色水团、茶酒供养。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递相宴赏。”从上述文字比较,成都的“端午”,似乎要比京城的简化一些。苏轼有词《六幺令·天中节》,或可探究蜀人端午的习俗:“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樽俎。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祭江诵君赋。感叹怀王昏聩,悲戚秦吞楚。异客垂涕淫淫,鬓白知几许?朝夕新亭对泣,泪竭陵阳处。汨罗江渚,湘累已逝,惟有万千断肠句。”▌宋代《清明上河图》(局部)但彼时,端午前后的大慈寺,因为有端午灯会,依然游人如织,陆游的《天中节前三日大圣慈寺华严阁燃灯甚盛游人过于元夕》写道:“万瓦如鳞百尺梯,遥看突兀与云齐。宝帘风定灯相射,绮陌尘香马不嘶。星陨半空天宇静,莲生陆地客心迷。归途细踏槐阴月,家在花行更向西。”到了清代,成都人的端午,主要是吃粽子,锦江以及附近郊县还会划龙舟,门上挂艾叶菖蒲,以及抹雄黄。六对山人的《锦城竹枝词》云:“龙舟锦水说端阳,艾叶菖蒲烧酒香。杂佩丛簪小儿女,都教耳鼻抹雄黄。”年,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学生陈慧权,在其毕业论文《成都节令风俗之研究》,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民国时成都人的端午节:成都人家,于端午清晨起床绝早,出门购菖蒲、艾叶,分悬于门旁,谓可以驱邪于门外,然后焚香秉烛,以粽子、皮蛋、盐蛋祀祖。祀毕,聚家人老小早餐,所供之肴,必有苋菜一碗,以大蒜捣泥加盐醋为调和,谓食之可以解毒,并能化除一年食肉吞下之毛,更饮雄黄伴和之酒,饮余之酒,再加大蒜,以指蘸“王”字于童孩之面额,并滴少许于两耳,即可避虫蛇毒螫,又其余,勾和以水,用柏枝蘸洒于屋之周遭,更倾其余沥于阴沟,谓如是则虫蛇走避,不扰于人。小儿女则着新衣,襟悬所缠之水粽,及绫绸所制之艾虎、小猴、香囊等以为点缀,蓉俗端午聚餐在晨,中秋餐在晚,故有“早端午,晚中秋”之说。午间,必以“洗澡药”煎汤沐浴,所谓“洗澡药”者,乃乡里小儿所采之药草,如泥鳅串、千里光、菖蒲、蒲公英、野菊花、陈艾、八角枫等,捆载背负,售之于市,谓以浴身可免疮毒疾患。药店则于此日,捕蟾蜍,取其眉株之酥,贮以待售,外科及针炙医师,则取艾制药,谓今日所作之药,特着灵效,并以此日午时新汲之水有毒,不可饮,饮之发疮,凡此种种虽不免于迷信,然亦吾国之最早卫生运动也。旧历五月,也是宋代成都人的扇市。但具体情况,并不见有详细的记载。清末时庆余的《成都月市竹枝词》记述扇市说:“扇市游人似锦丛,弃捐休说太匆匆。来年依旧深闺里,掩映桃花半面红。”想必宋时成都人的扇市,也如成都的锦市一样,让人眼花缭乱吧。唐人李淖的《秦中岁时记》载:“端午前两日,东市谓之扇市,车马特盛。”成都的扇市,或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在端午前后举行,也很有可能是在东门附近的大慈寺。▌南宋杨妹子《蔷薇诗》团扇,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南宋赵构《天山诗》团扇,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南宋李嵩《水殿招凉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成都有扇市,还有几个基础:一是本地盛产木材和竹子,扇子制作原料丰富;二是蜀中除了锦绣,“川纸”也是原料之一,而且不排除“扇市”也夹杂着川纸的展销,如有名的“薛涛笺”、谢公“十色笺”、广都纸、双流小灰纸等;另外,自唐以来,蜀中的能工巧匠和画家,有着深厚的沉淀,可谓制造扇子的人才济济。黄休复在《茅亭客话》中,记述西蜀擅长画竹的画家滕昌祐时说,其“所居州东北隅,竹树交阴,景象幽寂,有园圃池亭,徧莳花菓”,他的花园就种了慈竹、钓丝竹、丝竹(墨竹)、青竹、苦竹、柱竹等多个品种,“俗以五月十三日种竹多遭烈日晒干,园中竹以八月社前后。”当时蜀人“扇市”选择在五月,一是夏天的到来,二也是传统的栽竹之日“五月十三日”“竹醉日”(竹迷日)也在五月。“竹醉日”,其实是民间一个关于竹子的祭祀之日。宋代范致明的《岳阳风土记》就说:“五月十三日谓之龙生日,可种竹,《齐民要术》所谓竹醉日也。”《岁时广记·夏·竹迷日》引宋刘延世的《竹迷日种竹》诗说:“梅蒸方过有余润,竹醉由来自古云;掘地聊栽数竿竹,开帘还当一溪云。”“吴中近事君不知,团扇家家画放翁。”陆游诗中记下了宋代成都人流行的“团扇”,其《老学庵笔记》更记载:“宣和末……竹骨扇以木为柄,旧矣;忽变为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彻头’。”这种名为“不彻头”的短柄新式川扇,或一时成为成都人入夏的新宠。《金瓶梅词话》还记载了另一种洒金川扇——西门庆去见潘金莲时穿戴整齐,不忘“手拿洒金川扇儿”。南宋宁宗的杨皇后,以“杨妹子”之名留下了多幅书法之作,其中有多幅团扇,不知是否就有来自蜀地的产品。当她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在一帧团扇上题下“沦雪凝酥点嫩黄,蔷薇清露染衣裳。西风扫尽狂蜂蝶,独伴天边桂子香”的时候,是否会闻见一棵来自蜀地的竹子之清香。竹子,给蜀扇奠定了物质基础。《益部谈资》说:“川扇,不知起自何时,然李德裕有《画桐华凤扇赋》云:‘未若绘兹禽于素扇,动凉风于罗荐’,则唐时此地已尝制之矣。竹本蜀所富有,第不甚坚厚。纸则出嘉州彭县,轻细柔薄,惟可制扇,是其来已非一日,欲不充贡得乎?”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记载:“蜀锦、蜀扇、蜀杉,古今以为奇产。”谢肇淛撰《五杂俎》说:“蜀扇每岁进御,馈遗不下百余万。上以宫中所用,每柄率值黄金一两。”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四川贡扇》说:“聚骨扇,自吴制之外,惟川扇称佳。其精雅则宜士人,其华灿则宜艳女。”万历二十三年(),明神宗朱翊钧传旨,要四川布政使每年进贡各样龙凤扇八百一十柄,其式样及画面多达三十三种,可见明代蜀中扇子产业的传承。故此,明末清初人陈三岛的《川扇》诗说:“险离蚕丛地,要来宫扇传。大都白帝竹,出匣风初转。”需要指出的,后来的折扇,即“聚头扇”、“聚骨扇”“摺叠扇”,其实约在宋时由高丽传入,但到了明代以后才开始广为流行。明代陆深的《春雨堂随笔》记载:“今世所用摺叠扇,亦名聚头扇……东坡谓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许,正今摺扇。”明末韩泰华《无事为福斋随笔》则说是在明代永乐年间由日本传入:“东南使者持聚头扇,人皆讥笑之。我朝永乐初始有持者。及倭寇充贡,徧赐群臣,内府又倣其制,天下遂通用之。”“蜀民每岁五月,于大慈寺前街中卖扇,名扇市。”这是清嘉庆版《华阳县志》的记载。清代扇市的举办地点,或是宋代成都东门大慈寺扇市的沿袭。大慈寺,不但多次举办蚕市,官员宴席之所,相信也是五月扇市甚至六月香市的最佳举办地。《大清一统志》引《方舆胜览》就说:蜀民重蚕事,每岁二月望日,于府治东大慈寺前鬻蚕器,谓之蚕市。又五月九日于市前鬻香、药,号药市。……五月卖肩于街中,谓之扇市。”北宋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记载彼时的大慈寺,一片繁华,恍如闹市:“四方之人至于此者,徒见游手末伎,憧憧凑集,珍货奇巧,罗陈如市,只以为嬉戏炫鬻之所。”侯溥《寿宁院记》也描述这种罕见现象:“佛以静为乐,故凡塔庙,皆洁精谨严,屏远俗纷。独成都大慈寺,据圜匮之腹,商列贾次,茶炉药榜,篷占筵专,倡优杂戏之类,坌然其中,以游观之多而知一方之乐。”五月的成都,是如此热闹。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五月九日,有药市。五月十三日,老百姓们纷纷在房前屋后种竹。五月,还有盛极一时的扇市,挑着扇子的小贩,摊子上摆着扇子的商人,用一把把川扇,搧起了来自蜀地的竹子竹纸的一脉清香,悠远流长……▌成都市彭州宋代珍品银器窖藏
纳凉江渎,六月香市
淳熙四年()五月一日,陆游在《成都府江渎庙碑》中写道:“某尝登嶓冢之山,有泉涓涓出两山间,是为汉水之源,事与经合。及西游岷山,欲穷江源,而不可得。盖自蜀境之西,大山广谷,谽岈起伏,西南走蛮夷中,皆岷山也。则江所从来,尤荒远难知。”每一年祭祀江渎庙,或许都是古蜀人对来处蜀山岷江的一次次回望。
冬有“三九”、夏有“三伏”。农历六月,伴随着小暑与大暑,成都人迎来了最热的三伏。“六月,初伏日会监司,中伏日会职官以上,末伏日会府县官,皆就江渎庙设厅。初,文潞公(文彦博)建设厅,以伏日为会避暑,自是以为常。早宴罢,泛舟池中,复出,就厅晚宴。观者临池张饮,尽日为乐。”三伏天,成都太守会分别在初伏日与监司、中伏日与职官以上、末伏日与府县官相聚,在江渎庙一起避暑。为此,益州知州文彦博还特意在江渎庙修建了凉亭。早饭后,就会泛舟池中,出来后,再于江渎庙晚宴。这一天,也会带动老百姓纷纷出游江渎庙饮酒作乐。宋祁有《避暑江渎祠池》《江渎亭诗》《夏日江渎亭小饮诗》,田况有《伏日会江渎池》,吴中复有《江渎泛舟》,陆游有《江渎庙纳凉》。除了三伏天江渎庙避暑,成都人可能还在立夏这天于江渎庙祭祀江神,宋仁宗赵祯就下令,每年“立夏日祭江渎于成都府”。“江渎祠前有流水,欢注蓄泄为池塘。沈沈隆厦压平岸,好树荫亚芙蕖香。”从诗中看,江渎庙有点像一个微缩版的“湿地公园”。清末傅崇矩《成都通览》说,“古江渎池,即今之上莲花池也。伪蜀时中令赵史隐池中种藕,池岸种垂杨、芙蓉……”
江渎庙,即江渎祠,明代人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将其列为“南门之胜”。《元和志》卷三十一“成都县”载:江渎祠“在县南八里”。《寰宇记》卷七十二“华阳县”载:江渎祠“在县南上四里”。
▌洪芻撰《香谱》书页
▌明周嘉冑纂辑《香乘》书页,明崇祯十四年刊本,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
▌清张履平辑《坤德宝鉴》“香谱”书页,清乾隆42年遹修堂刊本,年
《括地志》云:“江渎祠在益州成都县南八里。秦并天下,江水祠蜀。”可见,秦始皇一统中国后,成都就建有“江渎祠”祭祀江神。隋开皇三年(),重建。唐玄宗天宝六年(),封江渎之神为广源公。宋太祖开宝六年(),“有诏自京师绘图遣工,侈大庙制”,重建江渎庙,以至“杰阁广殿,修廊邃宇,闻于天下”。
自唐代开始,江渎庙就一直位于城之西南,清康熙六年重建的江渎祠,位于今文庙西街石室中学对面,年彻底拆除。今四川省博物院存有明成化七年()所铸江渎神及二妃铜像,那青色铜像上的微光,仿佛还在诉说着昔日成都人以江渎庙为中心的避暑时光。
六月,宋时的成都人除了立夏祭祀江神,三伏避暑江渎庙,还会有一个买卖香料的会展式香市。当时,成都寺观众多,如大慈寺、宝历寺、梵安寺、净众寺、安福寺、圣寿寺、昭觉寺、玉局观、信相院、移忠院、大智院等,这也可能是众多寺观联合举办的一个盛会,香市搭配着庙会,而幽静清凉、古木众多、亭台楼榭的寺观又是三伏天避暑的好去处。
宋人叶廷圭《名香谱》所载的蝉蚕香、茵犀香、石叶香、百濯香、凤髓香、紫述香,相信这些奇香连同各地而来的异宝,以及吃的玩的,应该都能在成都的香市上见到。关于宋代成都的香市,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具体的举办中心,也可能像扇市一样在大慈寺,但彼时香市,它通往的地方,一定是西边的“河南道”。
▌宋代花鸟画细部
河南道是丝绸之路的一支,其起点就是益州(成都),终点是西域和漠北,因其沿线主要经过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吐谷浑河南国,故而又被称作丝绸之路之“河南道”。“河南道”连缀起了南北丝绸之路,也为敦煌、新疆乃至更远的地方,带去了蜀锦与蜀香。
今天,成都武侯祠旁,有两条十字交叉纵横的街道——武侯祠横街与洗面桥横街,被誉为成都的“八廓街”,川藏生产以及来自尼泊尔的藏传佛教用品,在这里汇集后又发往各大藏区。这里仿佛就是宋时成都香市的再现。
晚清庆余《成都月市竹枝词》追述香市说:“一声清磬悟禅机,古寺焚香上翠微。风送梵音齐发后,背人私祝藳砧归。”经历过元蒙铁蹄和明末清初兵火,清代成都的寺观早已不复宋时,何况曾经勾连四方的香市。然而,对于成都人来说,一线香烟袅袅,不管是浴佛日,还是七夕节,依然在这个上善若水的成都平原上一年年延续……
▌江渎祠供奉的江渎神及二妃铜像,明成化六年()铸造。四川博物院藏林元亨摄影
▌宋代《文会图》局部
▌传统绢绣献寿图
撰文林元亨供图
白郎林元亨邓平模主编
晨曦责编
Jamie美编
Birdy(上下滑动点击阅读)(上下滑动点击阅读)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